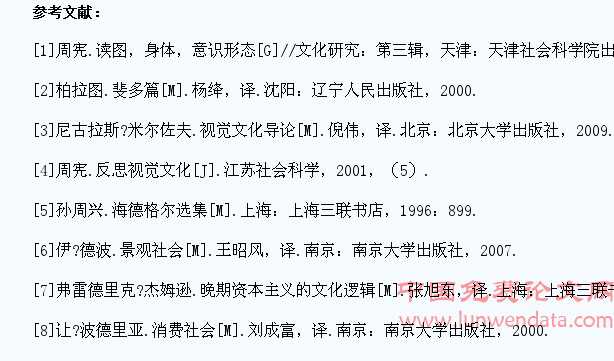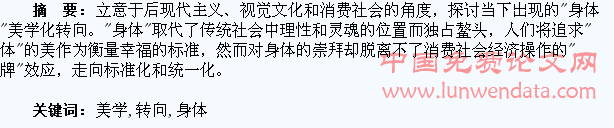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86-02
1、身体美学工厂
大家已不可以阻止自己将目光聚焦于“身体”这一物质存在,对它的关注度已上升到人类几千年历史之最。围绕着“身体”这一主题,好像掀起了一个巨大的“身体美学化”[1]浪潮,各色关于身体的产业使得全球好像都成为一个庞大的身体美学的工厂。走在街头,每个身体都衣着光鲜;广告里,身体元素的参与无处不在;医学界,大家对身体健康的关注现在恐怕要让坐落于对身体美的关注;甚至在文学界,“下半身”写作也已成为一种时尚和趋势。
然而,“身体”热并非原来即这样。从传统农耕社会到现代社会,身体历程了一个从功能性到美学性转变的过程,简单来看,“身体”有如下方面的变化:
一是身体从被压制到被解放。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儒家看来,身体需要用伦理道德去制约,以免耽溺于肉欲。至南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身体套上牢牢的枷锁。直至20世纪,伴随西方各种思潮的东来,身体才渐渐解放。在西方,身体也难免被压制的命。早在柏拉图时,“身体”就已被设置在了灵魂的对立面。他在《斐多篇》中觉得,死亡只不过身体的死亡而已,它是“灵魂和肉体的离别”[2]13。柏拉图确立了身体和灵魂的对立“二元论”,赞赏灵魂的不朽,而对身体嗤之以鼻。中世纪,教会和修道院的兴盛史则相对应地构成了“身体”的苦累史,教会主张苦行、祈祷、斋戒、克己,追求在对身体进行控制的过程中达到灵魂与上帝的同在。中世纪后,科学击退神学,理性占据了高地,但却也再一次将身体压制在了理性主义之下。直到20世纪,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福柯等才从理论上确立了身体在当下日常的要紧地位。
二是身体展示方法的古今不同。中国古时候文论对“言”与“意”的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最典型的是“得意忘言”说。这形成了古时候的审美观,重在言外之意而不求直露。因而在身体展示方面,自然不可以开口直言,言无不尽。譬如,《诗经》的《卫风?硕人》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即通过比喻来描绘了一个美人的姿态相貌,没直言,却给人无限遐想。反观当下现代社会,身体以图像化的形式不断展示在大家的眼前,它已剥去传统社会中蒙在身体表层的柔纱,将身体去魅,在身体美学化的过程中,使“身体”成为年代的要紧主题。
三是身体展示的形象之比较。传统社会中,人类的身体呈现出一个自然本真的状况,追求端庄、漂亮,并且愈加重视从内在精神上提高,通过修德养性来使外貌和精神达到和谐自然的境地。然而,伴随科技的进步,当下的身体已发生了千变万化。它更为崇尚人工美化,或化妆、或整形、或名贵服装。当下的身体同时出现的问题还有:身体的展示呈现出趋同化、标准化的倾向,如很多对“范冰冰”标准脸的模仿。
由上剖析可知,现代社会已出现“身体美学化”的转向,它取代了传统社会看重精神和理性的地方,独占鳌头。大家已将追求身体的美学化作为衡量幸福的规范,开始看重这个躯壳给大家带来的强烈满足感。但大家也看到,标准化了的身体是单调的、乏味的、浅薄的。那样,身体美学化的时尚从何而来?
2、视觉文化的后现代性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举推翻了理性的精神后台,以“反现代主义”的姿态横扫建筑界、文化界、艺术界,乃至大家的平时生活。它以消解现代主义的理性、中心化、统一性、标准化和深度感等为信条,做出了各种探索感性、本真自我、平面感的尝试。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后现代主义以它开放式的方案取得了大家的喜爱,叫人们畅游在感性的游戏中无法抗拒,在影像的狂欢中忘乎所以。
而视觉文化,则是后现代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觉得“后现代主义即视觉文化”,“视觉文化是一种方案,用它来研究后现代平时生活的谱系、概念和用途。大家称之为离别的、破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最好从视觉上加以想象和理解,就仿佛它在19世纪经典地呈目前报纸与小说中一样。”[3]4可见,视觉文化伴随后现代而来,后现代主义在胜利的欢庆中,携带大众迎来了视觉文化这一世界进程。
那样,何为视觉文化?在学者周宪的视觉文化研究中,大家看到了如此一段视觉文化的历史概括: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较早地提出视觉文化的定义,他敏锐地把握到电影将给人类认识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之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年代艺术理论,大大丰富了视觉文化定义的内涵;麦克卢汉从媒介和传播方法的变革角度,进一步论证了电子媒介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将视觉和听觉文化整理起来,对受众的成效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媒介[4]。很多视觉文化研究者都认识到了视觉文化对世界的改变,正如海德格尔说的,这是“世界图像的兴起:世界图像……并不是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如此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5]899
视觉文化的出现,不只引起了某些传统艺术形态和艺术观念的变革,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存活秩序。它具备以下几种倾向:
1.视觉的独裁性。法国哲学家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了视觉图像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1)世界转化为形象,就是把人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转化为被动的行为;(2)在景观社会中,视觉具备优先性和至上性,它压倒了其他观感,现代人完全成了观者;(3)影像避开了人的活动而转向景观的观看,从根本上说,景观就是独裁和暴力,它不允许对话。”[6]由此大家可知,视觉图像一方面是常见的,同时也具备不可抗拒性,是独裁的。 2.视觉的平面性。后现代主义以否定深度、理性、中心等为身份标签,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形成了不一样的文化特点,并力图将后者消解掉。观众在视觉文化中可以直接拥有强烈的感官享受,让娱乐成为大家追求的目的,快乐成为唯一的原则,而审美也被停留于表层,以此成为新的观看、理解世界的方法。
回过头,大家来看看“身体”。“身体”是大家日常最易目之所及之物,审美化时尚自然要纳之入怀,使之成为视觉文化的主力大军。视觉文化所具备的后现代特点都显著地体目前了“身体”这一要点之上。后现代感性直观的需要使身体挣脱了传统伦理道德和灵魂的压制,伴随视觉图像风靡,身体也以震惊视觉的方法猛然亮相,大家在身体的狂欢中赞叹着自由,畅享快感所带来的娱乐和满足感。
3、消费社会和视觉文化的联姻:身体的符号学转向
那样,为什么当下的“身体”会显示出统一的、单调的、乏味的时尚倾向呢?消费社会对此做出了回答。消费社会制造了一个不真实的观念:审美选择的无穷无尽。但事实上,透过消费社会的本质,大家只能看见标准化和符号化。
20世纪60年代,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大家的物质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渐渐由以生产为主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主的社会转型。大家可以说,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当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联姻,很大地推进了生活每个方面的审美化进步。而之所以出现了标准统一化的视觉图像,则根来自于消费社会的利益驱动性。
美国后现代主义大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对此说道,“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产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产品社会的规律驱使大家不断出产日新月异的货品,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本钱赚回,并且把收益不断地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势必遭到很多限制”[7]423。这是消费社会的经济操作,可见艺术与经济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身体”在消费社会中也被看作了产品,它逃离不掉被经济操作的命。法国哲学家让?波德莱尔对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做出了独特的研究。他指出,“身体”已发生了符号学的转向。在传统社会中,大家重视身体的用法价值,所以有奴隶市场或人肉买卖,而消费社会关注身体的符号意义,所以有各种选美或粉。视觉图像赋予身体的美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出于本性的对于漂亮的追求,而变成了一种资本,成为流行的一种形式。“漂亮的逻辑,同样也是流行的逻辑,可以被界定为身体的所有具体价值、‘实用价值’向唯一一种功用性‘交换价值’的蜕变,它通过抽象化将光荣的、健全的身体的观念、欲望和享乐的观念概括为它一个――且由此而当然地否定并忘却它们的现实直到在符号交换中耗竭。”[8]157此时,“身体”的偶像崇拜效应充分显示了出来,时髦也开始走在了尖端,大家抱着“名牌”理念去对身体做出各式改变,用身体去与消费社会做一次交换,以此证明我们的身份。这是一种身份认可的新的形式,大家在这种追随中获得了满足感。然而,当选择只限于消费社会规定的形式时,出现那样多的“范冰冰”也就不奇怪了。
视觉文化在当今的霸权地位已无可争议,图像崇拜和狂欢正成为当下平时生活的文化范式。然而,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共谋,在当下正形成了一个火烧眉毛的视觉危机。当大家沉醉于统一化了的直观快感中时,怎么办“身体”不可以承受之轻的问题真的值得大家去考虑。